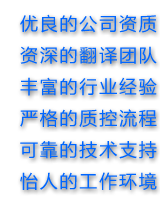众翻译学者对翻译的理解

对翻译的理解,可以说是见仁见智,无论是学者还是译员或者翻译专业的学生对翻译都有自己的认识,一起来看一下众翻译学者对翻译的理解:
王家新:译诗不仅要有“个性” 还要有“牺牲”
在一次交流会议主题致辞中,王家新指出:翻译被提升到一种本体论的高度。他引用波德莱尔“诗人作为译者”的定义,认为到了波德莱尔,存在的问题就变成了一个“翻译”的问题,人类的语言文化包括诗人的写作本身就带有一种翻译的性质。我们至今仍在背负着如雪莱所说的“巴别塔的诅咒”。自巴别塔之后,翻译就成为了人类的宿命,恰如乔治?斯坦纳所说,“我们的文学是巴别塔的儿女”。在他看来,东方和西方都有着自己的诗人译诗传统,中国现代新诗的历史,也一直伴随着翻译。翻译推动着诗歌的变革和刷新,翻译创造了一种奇异的“语言的回声”。乔治?斯坦纳说“伟大的翻译比伟大的文学更为少见”。他认为伟大的翻译本身即是伟大的文学。创作和翻译构成了在座许多诗人写作生涯的“对位法”。他认为每个人身上都携带着一个译者,今天这次会议正是要让他“开口说话”。诗人译诗不仅要有“个性”,还必须要有“牺牲”。译者要有个性,但同时要奉行“非个人化”诗学原则,翻译本身就应是一种奉献和牺牲。一、本雅明认为翻译是两种语言的相遇中对“纯语言”的发掘;二,艾略特认为庞德不是翻译而是在英语中“发明”了中国诗。这些,都突显出翻译的重要意义。
顾彬:没有翻译 社会无法发展
著名汉学家、翻译家、诗人顾彬从对中国翻译界的印象入手谈论了翻译的重要性。他指出中国人不珍视翻译、译者。对于翻译,一种流行的说法是“人人都可以做翻译”,对于译者,也经常有说某人“仅仅是个译者”这类轻视的声音出现。德国有200多年翻译的历史,从歌德开始,包括里尔克、策兰等一流作家在内都搞翻译,其重要原因在于,翻译可以扩大母语,并在母语中引入另外的世界。顾彬认为一个社会如果没有翻译的话是无法发展的。翻译本身也是社会状况的重要反射角度。上个世纪30、40年代的德国,拒绝翻译,很野蛮,二战以后,翻译发展迅速,就像德国社会一样。
西川:语言和文化障碍构成诗歌的临界
诗人西川首先说自己出过五本译作,但以后不会再做翻译了,说他有点不大适合做翻译。随后他指出三种翻译的类型:学院派翻译(academic)、专业翻译(professional)、诗人翻译(poets)。2003年“非典”期间,他翻译了《米沃什词典》,由于不懂波兰语,他实际上是从英文进行的转译。出版社之所以请他,不是因为他是专业的翻译,而是考虑到他是位诗人。翻译米沃什的经历让西川意识到语言和文化障碍可能构成诗人在世界范围内认识诗歌的临界,自身的语言限度会阻碍其诗歌视界的广度,他认为这是目前诗歌翻译界所面临的问题。西川进一步指出,在面对一些小语种诗歌的翻译工作时,译者的身份问题就变得尤其微妙。有些人懂小语种,但自身不是诗人,那么翻译的质量就会产生疑问。
杨炼:庞德在英语中“发明”了中国诗
面对翻译的现状,活跃于国际诗坛的杨炼认为诗人有责任将诗歌的思想地图通过翻译传达给更多的人,而不是等待。有一次他阅读一位德语诗人的英译本,发现英译本有很多错误,他虽然按照英译本将其转译成中文,但凭借自己的直感,最后的中译本要比英译本更接近德语原文。当面对极为偏僻的小语种,需要从第三、第四甚至第五语言进行转移时,翻译就更像是一种观念的项目了,此过程中丢失的东西太多了。有一次他组织翻译一部用肯尼亚国内方言写的极富音乐性的诗集时,为了最大限度地保留其音乐性,杨炼叮嘱两位中文译者(一位是杨小滨,他将其译成上海方言;另一位是廖慧,将其译成四川方言)一定要运用方言口音并押韵,以保障译笔的音乐性。
杨炼也谈到了翻译的创造性意义。他援引本雅明“诗歌是第三种语言”这一说法,说翻译是“大海的第三岸”(这一表述出自他本人的诗中),诗人与译者之间是一种对话关系,二者在对话中重塑了译作这第三种文本,它介于限定与发明之间。庞德的翻译就是最好的证明:他对中国古诗的翻译对东西方的现代诗人们产生了双重的启示。
唐晓渡:特殊年代 译诗成为麻醉剂
著名诗评家唐晓渡的发言首先谈到从事翻译对于个人的重要意义。从文化匮乏的岁月走过来,唐晓渡深感若无翻译,他们这一代人的诗歌教养是不可想象的。他与翻译发生密切联系,是在90年代初,究其原因,是面对80年代末尾的社会历史事件,自己和当时很多人一样,陷入了无以言表的复杂感情之中,自己当时无法写作,也无法阅读,译诗是当时身陷耻辱与沉痛必然做出的选择。在进行翻译时,获得一种麻醉感,并以此忘掉肉身的痛苦。唐晓渡说道,诗歌翻译与诗歌创作一样,在特殊时刻具有拯救意义,使人增加对诗歌的感恩之心。他当时最早的翻译是美国女诗人西尔维亚?普拉斯,由于对现有译作不满意,他自己决定进行翻译,但是普拉斯的速度、节奏和意象间的折射使得翻译工作具有很大难度。后来,他的翻译兴趣转向了东欧诗人如赫伯特、米沃什等。唐晓渡认为,借助翻译,自己可感到诗歌的自在世界,扩展自己的诗歌理解。他也译过会昆德拉的“小说的艺术”,他把它当作诗论来读。
陈育虹:如何在翻译中“成为”原作诗人
台湾女诗人、翻译家陈育虹有不同的看法。首先,她表示自己非常看重激情和欲望对于翻译的重要性。她写诗写得很早,但开始翻译则是写诗20年以后的事情了。她的首个翻译对象是古希腊女诗人萨福。对她来说,翻译有时候是要为自己找到一个互补的声音,就像一件刺绣的两面。她认为翻译中体现的译者个人风格是重要的。作为一个诗人译者,她认为翻译不仅需要译者对两种语言都有很好的理解力和驾驭力,而且需要在翻译中“成为”原作诗人。她认为诗歌翻译就像是表演,译者需要切身地进入角色,进行严格语言转换;同时翻译又像是驯兽师,其工作目的即在于使两种语言进行合作表演。她举著名女演员朱丽叶?比诺什为例,说翻译就如表演一样,一个好的演员去饰演其他人,虽然惟妙惟肖,但仍然可见个人的艺术风格。
平田俊子:当下的诗歌翻译缺少历史动力
日本女诗人平田俊子谈论了日本文学翻译的情况。日本的文学翻译是从江户时代、明治维新以后开始的,当时有几位翻译家最早将英法诗歌译入了日语之中。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法国诗歌在日本大受欢迎,尤以法国诗人普列维尔为甚,当时对他的翻译,比较有名的是翻译家小栗原丰树(这是他做翻译的笔名,做创作的笔名是岩田宏)。近些年来,日本的文学翻译少了,且以小说居多,诗歌翻译不仅数量稀少,而且也仅是传达意义而已,已少有诗之韵味。即使有少量的诗歌翻译,也很少被人阅读,只有一些诺奖得主的作品才有人去读,比如辛波斯卡、特朗斯特罗姆等。当下的诗歌翻译因缺少历史动力,数量与质量下滑明显,因而日本诗歌界很少参与到世界诗坛的互动当中。
卡尔聂奇:诗人是诗歌最好译者
罗马尼亚女诗人、现任罗马尼亚笔会主席卡尔聂奇从更大的视角出发,认为在当下多元文化彼此碰撞的社会处境中,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地都在进行着翻译。翻译对于年轻一代很重要。翻译不仅是一种诗歌的教育,更是对语言的训练,因为要做好翻译,我们必须要了解语言背后的文化、历史。她自己在学生时代尝试翻译了很多英美诗人,因此使自己更多地了解了他们。在法国生活多年,卡尔聂奇翻译了很多法语诗人,法国的生活使她深感法国与罗马尼亚之间文化差异的巨大,这种差异也必然投射在两种语言之中:在把法语诗歌译入罗马尼亚语时,她深深意识到了两种语言各自的局限。正是意识到了局限的存在,翻译也因此构成了对自己语言的丰富。对于诗歌翻译来说,卡尔聂奇赞同诗人是诗歌最好译者的观点,因为诗人对于语词间的张力、能量和背后的文化有着比常人更多的理解和敏感。做诗歌翻译意味着思维的扩展,人们在翻译中逐渐获得了思维的宇宙的维度,它也会扩展我们的心灵和我们对现实的理解——翻译是永存的。
维克多:最好的阅读方式是翻译
来自古巴、同时又在美国任教的西班牙语诗人维克多?罗格里格斯?努涅斯在其发言中强调了翻译超越语言和文化碰撞、对话的重要性。他认为“没有翻译,很多文化是不可见的”。他认为语言内部有着文化的深层结构,因此最好的阅读方式即是翻译。翻译不仅关涉着语言,同时也是两种文化的深层对话。接着他谈到了翻译在美国的现状。他说译者在美国不被看作学者、作家,而且也无法在大学里拿到全职的教职,尽管译作的出版量巨大:过去五年里,美国出版的重要书籍几乎都是译作,包括餐饮、科学等许多领域,然而在其中文学类书籍的比重仅为5%,诗歌的比重则少之又少。美国一年出版4万本译作,但是从西班牙语译入的诗歌仅有12本,特别是重要的西语诗人如聂鲁达等,他们的英文译本质量都很粗糙,让人不满意,对于努涅斯来说,这是个巨大的刺激,刺激他努力进行西语诗歌的译介工作。他迄今已有15本译作,其中一些是与美国译者合作完成的,他审慎地认为很少有人能真正精通两种语言,并跨越两种文化来进行翻译,因此他觉得找精通英语的合作者是非常必要的。翻译是个文化问题,它超过了语言问题,从这一角度看,最杰出的西语诗人目前尚未很好地译入英语之中。
穆迪格:翻译诺奖,诗人呈现出不同的难度
瑞典诗人穆迪格直言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出版人构成了自己的重要身份,他出版过布罗茨基、沃尔科特等人的作品,直到退休以后才重回诗人的行列之中,尽管1968年他自己已经出版过诗集了。做出版使他结识了许多重要的诗人,通过与这些不同国籍、不同语言的诗人们相接触,穆迪格深感翻译之重要,不仅重要,也非常困难和复杂,尤其是当我们在面对语言才能高超、文化背景复杂的诗人时。比如一些诺奖得主如布罗茨基、沃尔科特、索因卡等,他们每个人都呈现出不同的难度。在他的接触中,布罗茨基要求其瑞典语译者紧贴文本,要语言正确,因此要给自己寻找译者的话,他更倾向于精通语言的忠实的翻译,而不是诗人翻译。沃尔科特诗中有加勒比海地区多元文化的成分,非常诙谐幽默,如何将这一特质翻译过来,是翻译沃尔科特的难度。而索因卡的诗歌中则包含着尼日利亚的传统,要翻译他的诗歌,我们需要深入尼日利亚的文化传统之中,去感受其中的深奥和神秘。穆迪格还提到了美国诗人罗伯特?勃莱与特朗斯特罗姆的通信集《航空信》,二者在里面谈论了很多关于诗歌翻译的有趣的问题。穆迪格认为翻译要有开放的心态,要有自己的解决方法,但不能不考虑原作。他本人也曾对多位不同文化背景的诗人作品进行翻译,不仅是文本表层的语言结构、文本背后复杂的民族传统对翻译活动也构成了挑战。
伊尔玛:诗人如何在翻译中克制自己
精通多种语言的瑞士德语著名诗人、德国语言文学院院士伊尔玛?拉库萨首先发言。她从自己具有多种语言文化的家庭背景出发,说自己“生来就是一位译者”。她十七岁开始写诗,翻译的首个对象是俄国女诗人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她坦承当时的翻译其实具有很强的散文性。拉库萨认为俄语诗歌非常难译,因为它具有强烈的结构感和韵律,这些品质在翻译中是不能被轻易忽略的。迄今为止,她翻译过茨维塔耶娃的诗歌、剧作、散文和信件,也翻译过法国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和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等作家的作品。拉库萨认为翻译是一种对话,其关键是如何在译作中准确再现原作者的个人风格。也就是说,译者要思考如何不让自己的风格去影响自己的译作这一问题,拉库萨给出的建议是要去努力揣摩原作者,让自己的耳朵尽可能地向对方打开。拉库萨所持的是“直译”的翻译观,她认为保罗?策兰在对曼德尔施塔姆、艾米莉.狄金森等诗人的翻译中包含了过多的个人风格,“策兰是天才,他的翻译总是带有他本人的影子”,拉库萨对此有所保留。对她来说,直译极富挑战,诗人如何在翻译中克制自己,而尽力将原作的声音传达出来,这是她一直要解决的问题。
——兰州翻译公司
译声兰州翻译公司目前是国内专业的翻译机构之一,译声兰州翻译公司秉承“诚信 专业”的服务理念,为国内外客户提供一流翻译服务。了解更多信息:请直接致电:400-600-6870咨询。
发表评论:

上一篇: 文学翻译是复制还是改写?
下一篇: 熊猫什么会这么懒